
根据身份证显示,老林是1952年10月15日出生在台湾省宜兰县的。
今年他70岁,终于到了“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时候。
今年年中时我还惦记这个事,想着到金秋的时候要过去给他个惊喜。要是2020年前,其实就悄悄的过去就行了,但现在进入北大需要过三关斩六将,各种码各种证明自己清白的证据,人还没见到,阵仗已经很大,想搞点什么“SURPRISE”那是妄念了。
今年10月开始,我因为要出差,肉身时不时被北京的弹窗锁住,锁了以后就流浪外地,过着晨昏颠倒的生活,什么正事都有点糊里糊涂。昨天晚上看到群里有熟人写的文章,说开了林老师70岁生日&从教35周年的学术讨论会,这才一拍脑袋,哎呀,感觉自己已经未老先衰记忆力缺失了。
我是2011年认识林老师的。至今记得那个场景,盛夏未名湖,垂柳依依,蛙声零星,老林白衬衣深灰裤子——后来发现那是他的标准装束。他高大挺拔,发色微微灰白,脸上微笑温和而笃定——后来也发现,那是他的招牌式微笑,除非在很私人的场合和情绪波动的时候,那个笑容才会敛去。
一晃十多年,当年自己还是剪着短发的,圆圆眼的懵懂的年轻助理教授,当时老林还是世界银行的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正在为“中国增长模式”的全球普及奔忙,时间如白驹过隙,今年春天带着已经4岁的娃去见林老师的时候,他眼角皱纹已经深了不少,发色染霜了不少,只有脊背始终如一,犹如青松一般挺直。
是,老林始终有少年气。在他澄静温和的眼神下,永远有一簇火焰燃烧,对理想,对自己的理论,理念,和信念。我想,即使80,90了,他也仍然会这样,会继续丰富新结构经济学的内核,拓展新结构经济学的边界。
结构,是经济的灵魂。没有结构的经济学是虚的。其实这几年,我一年比一年的理解了这一点。
早上发微信给他,说,“祝您一面从心所欲不逾矩,一面永远保持鲜衣怒马的少年气。脊背永远如松,眼神永远清亮,永远温和又愤怒。”
以一篇5年前的旧文为贺。
林毅夫,JUSTIN LIN,这个名字,注定要和这个波澜壮阔的时代相遇交汇,再超越时代。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孔子《论语·泰伯章》
想起林毅夫老师,我脑子里跳出的第一个词语竟然是“孤独”。闭上眼浮现出的,是一个挺拔的高大背影,不知疲倦地走在一条宽阔的、但车流稀疏的大路之上。阳光从他肩上滑落,落在地上的影子,倔强中透着一丝寂寥。
对于我们前后好几代的经济学子来说,林毅夫以及他创立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曾经是殿堂级的现象,当年CCER几大创始人,海闻,张维迎,易纲…..每个人都是一出波澜壮阔的时代大剧,宋国青,周其仁等元老教授则以其无与伦比的犀利和深刻,多年如一日站在中国宏微观经济学的巅峰。这个机构曾代表了传奇,热血,和中国士大夫“经世济民”的终极理想。
林老师毋庸置疑是个中典范。从台湾的“十大杰出青年”,凫水渡过海峡的林正义,到北大学子,芝加哥大学博士,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所副所长林毅夫,再到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创始人,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林毅夫,再到“新结构经济学”创始人和倡导者林毅夫……在“国之重器,著名经济学家”的耀眼光芒下,他与稚儿妻子一别四年,辗转万里在美国相见;他永诀家园,生不能养,死不能送,只能伏地恸哭遥祭父母;他一反“知识分子”弱不禁风的姿态,在北大校园拔拳怒怼泼皮暴发户…..他一生的跌宕起伏,荡气回肠,真真有如这个时代“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的风云际会。
有的人,注定要和时代相遇交汇,再超越时代。
我第一次正儿八经读林毅夫老师的书,是出国不久的一个夏天。当时因为SAS,机票便宜得难以置信,800加币往返,中途在日本转机。旅途漫长,我将从国内带来的一本《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放进了背包。那个时候林毅夫的名声已经如日中天,但是我生性懒散,除了啃必须啃的专业书外,更喜欢在网上游荡,对于大部头的文章,一直有点敬而远之。这次倒是好,机舱里被隔绝得人事两茫茫,反而静了心读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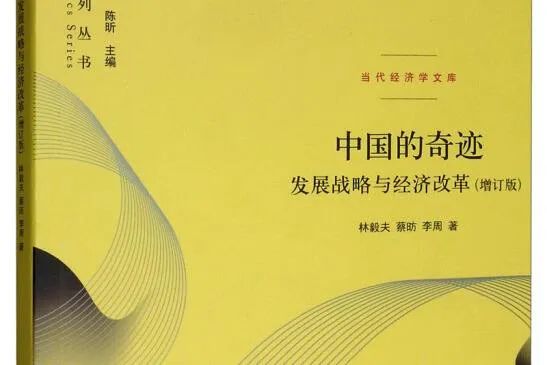
我们这代人恰好成长在中国经济以不可思议的速度飞速发展的时代,父母念叨的贫穷和童年时代隐约的匮缺记忆很快被滚滚而来的物质湮没,“增长”对我们而言,更像是个自然的结果。作为一个金融学专业的学生,我对市场的认是“理所当然”,很少会去思考市场背后的“制度”和“演化变迁”。但在这次20个小时的飞行中,我将这本不算“轻松好看”的书读完了,脑子里飞速闪过的是自己从小到大的很多事情,看过的很多农村题材小说,父母念叨过的很多历史,甚至课堂上折磨过我的各种增长理论,Harrod-Domar模型,Solow模型,都以一种奇怪的方式都涌入我大脑——“经济增长”第一次在我脑中有了具象的涵义,我从小到大所经历的一切原来都是源自一个“增长奇迹”,而这个奇迹,是要素禀赋与制度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也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框架性思维的重要性。大道至简,很多事情,看似眼花缭乱,纷繁芜杂,但是一旦立足框架,就迎刃而解。
我对写出这本书的人充满了敬意和说不出的好感。林毅夫这个名字,也从一个“与我无关的超级大牛经济学家”成为了“影响我的一本书的作者”。这中间的微妙分别,大概只有当事人明白。但是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和这么个牛人有什么交集。
世界上的事情倒是很奇妙。我2010年我回国,去了北大光华教书,自然的与北大经济学圈子里的人熟悉了起来。最先见到的是大名鼎鼎的“中国宏观第一人”宋国青老师。初次见面在他蓝旗营的家里,大概只有三,五句话的功夫,老爷子对我的特点(强项和弱点)就了解得一清二楚。聪明无双,大概就是指这样的人吧。但犀利之外,他又显得很小孩子气,嘟囔抱怨自己的牙齿不好,但是怕疼,不愿去“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种牙,充分流露出对于咬不动的食物又爱又恨的心事,逗得我哈哈大笑。
见到林毅夫老师则是2011年的夏天了,大概是7月份吧,我和徐远在校园里瞎逛,盛夏的未名湖垂柳依依,蛙声零星,远远看见几个人站在湖边,徐远突然惊呼一声“林老师”,拉我跑过去,我这才知道,面前这个穿白色衬衣的高大的中年男子,就是传说中的林毅夫。

因为有见老宋的经验,我全无初次见“大牛”的局促拘束。那时候老林还在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的任上,我记得他们在聊这几年在发展中国家调研的感触和经验,我家里做外贸和海外投资的,对有些国家略知道点皮毛,也就信口开河的插嘴乱说。林老师居然听得很认真,然后很认真的一一给出自己的判断,他的眼神如此专注,表达如此诚恳,我怀疑他的人生字典里从没有“敷衍”这个词语——后来证明,这个怀疑是对的。
2012年之后,林老师回国。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开始力推“新结构经济学”。在他的办公室里,他在《繁荣的求索》和《本体和常无》两本书上用心的签好自己的名字,很郑重地递给我,嘱咐我好好读,好好思考。

那时候我还忙着写象牙塔的学术论文,匆匆把《繁荣的求索》看完了,大体上明白了老师是顺着《中国的奇迹》的思路在拓展衍生,他在前些年归纳总结中国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观察到的绝大多数国家的发展路径,讨论一种经济学的新框架性思维,这个框架把经济增长的“前提”作为一个重要的变量考虑进来:一个经济体在某个发展阶段的增长不是简单的“市场化”的结果,而必须考虑这个阶段的要素禀赋结构,因此,与其相适应的产业结构和市场基础设施(i.e.,道路,交通,通讯,金融,法律,市场管制等软硬基础设施)就会对经济增长起到关键作用。
当年我模模糊糊觉得这个方向是对的,但是想得不是很透彻,也就放下了。2013年,我痛下决心告别纯粹的象牙塔学问,开始大量地作企业实地调研。从山东的日照钢铁,到湖南的三一重工,从上海的上实投资,张江集团,到浙江的大批中小民营企业;2015我开始研究中国的互联网企业,从盛大,九城,完美世界,到蚂蚁金服,天神娱乐——中国的企业史,就是一部改革以来的经济史,所以被逼着将中国改革这几十年的历程梳理了一遍,然后我常常到老师那儿去聊会儿天,主要是聊自己在外面看到的很多现象,听听林老师的意见。每次他都饶有兴趣的听我说这些微观的事情。他参观过三一,对于三一从德国制造的“学生”到“主人”(注:2012年,三一收购了曾被自己追赶多年的德国王牌混凝土机械制造商普茨迈斯特)的过程很感兴趣,一直追问在“追赶”到“超越”的过程中,企业做对了什么。在这些细节基础上,他又总会回到要素禀赋和产业结构,做出自己的判断。
我当时已经感到在互联网企业这一块,中国某些企业具有自己独特的性质和竞争力,所以问老师对现在的互联网企业怎么看?那次我记得林老师沉吟了一下,非常坦诚的说,互联网这一块我研究不多,但是我想思路可能有某种相似。他给我仔细的讲述了新结构的五类产业划分,传统型,追赶型,领先型,弯道超车型,以及基础研发型。今天的中国作为中等收入国家,在人力资本方面还具有较大的比较优势,所以某些新兴科技行业,比如移动通信行业,研究成本相对低,研发周期短,应用快,而中国具有13亿人口的应用市场,技术应用型的企业可能发生化学反应,有希望实现对发达国家的弯道超车,他举了小米做例子。
过了好几个月,一个回国讲学的朋友和我聊天,突然问我,为什么国内生活这么方便,点餐,购物,打车,什么都一个手机搞定。他是个严肃的经济学者,提出这个问题也是严肃探究的,我突然想起了老林说的“弯道超车”的概念,然后发现从这个方向上,中国很多互联网的独角兽企业,i.e.,美团,滴滴,都变得更容易理解。
2016年好几件事情让我对林老师的理论有了新的认识。第一件事是我开始疯魔般的看蚂蚁金服这个案例,虽然至今还处在魔障中,但是发现老林的逻辑是有很强解释力的。早期的支付宝就属于“研发周期短,研发成本不高,应用快”的产品,因为当时的中国是深度金融抑制的国家,为淘宝的担保交易提供了无限广阔的场景,所以支付宝迅速“弯道超车”——今天中国在移动支付方面,已经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了。更有意思的是,因为巨大的应用场景支持,支付宝有了不停“迭代试错”的机会和实力,又反过来促进了研发,如今蚂蚁旗下的第四代支付宝,在技术上已经处于全球领先的地位,率先实现了对印度和东南亚沿线国家的“技术输出”,在应用上“弯道超车”之后,技术上也实现了“弯道超车”。
第二件是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林张产业政策之争。我是维迎老师招进北大光华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这代人都受过他的市场思想启蒙,对政府的手保持着天然的警惕。这几年我在现实世界里的观察,又觉得林老师讲的很多道理都特别准确。我在上海看完了辩论的直播,其实两位老师的理论都比较熟悉,现场讲的内容倒也没有出乎意外,但给了我一次重新审视中国经济发展路径的机会。在要不要产业政策上,林张看似持着截然相反的态度:维迎老师认为政府无法制定有效的产业政策,所以不应该要产业政策,毅夫老师强调政府应该通过制定与现阶段要素禀赋相适应的产业政策,实现更好的挖掘增长潜力的产业结构。一个花甲,一个半百的两位老先生在台上唇枪舌战,加上黄益平老师风度翩翩的主持,特别有北大思辨的精神气质。但是后来我仔细琢磨,他俩的讨论其实没有在一个频道上。

张老师强调的是一个理想的状态:市场不存在太多扭曲,市场价格是最好的信号,任何人为的干涉都会破坏这个信号机制。他的思路更像哈耶克,是要求“回到斯密”,回到最基本的理性。林老师强调的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发展是路径相依的,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其要素禀赋有其适配的产业结构,由于外部性的存在,企业的行为不是社会最优的,政府在市场基础设施改进方面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他的思路,更接近凯恩斯强调波动的存在,因而强调调控的必要。
哈耶克和凯恩斯之争,也是闹腾了近80年的话题了。经济学讲究一个“一般均衡”,哈耶克要求让市场去寻找均衡,政府的上帝之手需要控制到最小,而凯恩斯则认为,市场存在不完美(比如动物精神),谁也不知道均衡在哪里,所以市场会有巨大的波动,政府需要一定调控。
如果我们再往历史的细节里面挖掘,就会发现,其实哈耶克和凯恩斯理论都是有很强的时代特征和地域性的。哈耶克是奥地利学派的鼻祖,这一派针锋相对的是当时正在盛行的苏联计划经济模式——1917年之后,苏联模式在学术圈一直拥趸不少(著名的萨缪尔森就不只一次的公开赞美苏联模式是最好的经济模式)。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是在这么一个靶子下写出来的,“市场价格是最好的信号”是针对苏联政府从头到脚的“上帝之手”而言的。而凯恩斯是英国财政大臣,他的《通论》的出发点和思考路径都是在已经完成思想启蒙和工业革命的英国的框架下进行的,一战前后发生在英美的巨大经济波动引起了他的警觉。
让一个被绑缚得死死的人解开枷锁,和对一个精壮的年轻人谈运动规则——这是这两本宏伟巨著的时代大背景。尽管两本书都具有跨时代的一般性,但是写作从来不是完全客观的描述,学术观点更是一种主观意识下的客观表达而已。所以在我的脑子里(也许是我对理论的理解肤浅吧),我从来没有觉得哈耶克和凯恩斯不相容过,他们在我脑中不过是均衡的不同维度,均衡本来就是复杂的,就像人性从来无法用黑白是非简单区分。
同样的逻辑,维迎老师针对的是中国仍然存在的各种市场扭曲,要求从根本上改变这些扭曲,达到一个理想的状态(市场干预少,摩擦少,市场机制运行良好)。毅夫老师针对的是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发展中”和“转型中”,认为从传统农业经济到高收入现代工业化经济的发展不是跳跃式的,而是分布在一个连续频谱之上,对应着与这个阶段相适应的禀赋结构,要求掌握着大量资源的政府“有为”,去改善市场基础设施,帮助市场发育。维迎老师希望政府放弃权力和资源,毅夫老师则承认政府拥有权力和资源的现实,希望政府合理的使用权力,配置资源。
在家里吃饭的时候,谈起对林张理论的想法,家里正好有人经历了从体制内到体制外的转变,对于产业政策这一块特别敏感。她的阐述完全印证了我的想法,维迎老师和毅夫老师讲的是中国现状的不同维度:
一方面,盲目的产业政策害了不少产业,一个典型的是动漫行业,当年国家要求支持动漫行业,然后各级政府就开始大撒币,她所在的产业园里一夜之间多了无数“动漫公司”,大多是来混政府补贴,搞寻租的,然后几年过去灰飞烟灭,动漫行业一直暮气沉沉,反观网游行业,是当年不够重视,限制,管控和“支持”都比较较少,大体上类似负面清单式的管理,反而发展得蓬蓬勃勃。
但是在另外一个方面,从传统演化和现实发展的情况来看,中国政府历来是强政府。从一个巨大的计划经济转型,经过了几十年的高速增长,尤其是近二十年的土地财政之后,体制内沉淀的巨大资源和体制的巨大惯性,都是现实的约束条件,这不是一句“改革”就可以改变的。她告诉我,在现实条件下,很多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在土地,政策,资金,甚至人才储备等很多微观层面,都需要当地政府的支持和配合。
很多企业不是不需要产业政策,而是需要“懂企业的”的政策。但在现实中小企业和政府之间是割裂的,存在着巨大信息不对称——中国的“熟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信息不对称导致的结果。因此,解决政企之间信息不对称,让双方的信息可以反馈,将政府的巨大存量资源匹配到企业,通过企业的成长实现政府资源的流动性。这种“匹配”的本身就是创造价值的,是用市场的方法解决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博弈——这不是一涌而上的智库专家能完成的,而是需要一些来自企业,扎根企业,熟悉政府,超越政府的专业队伍去推动和完成。相比“改革”的呼唤,这种“行动”应该算是寻找去现实约束中的次优选择吧。

坦白说,只要是社会科学的理论,就难免被标签化。张维迎老师容易被贴上“反政府”的标签,而林毅夫老师的理论则更容易被滥用,因而容易被批评为“为政府背书”。在市场被当作宗教的环境里,林毅夫被骂的风险更高一些。但市场,却从来都不是免费的,作为“迄今人类历史发现的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机制,(市场)不是免费的,而且很昂贵,建立和维护都需要耗费很多资源”。而林毅夫理解了这个约束,并力图在这个约束下,找出跨越约束的现实方案。
在我眼里,维迎老师是我们这个时代市场的思想启蒙者,具有殉道者一般的理想主义光芒,而毅夫老师则是这个时代市场理想的践行者,在现实约束中,积硅步以致千里。他为这个理想,所付出的,不仅仅是几十年如一日的苦行僧一般自律,严谨,勤奋,还需要承担不被时代理解的风险。
几年下来,我看到林老师修得极短极平的寸头多了些灰白色的痕迹,眼角也多了些皱纹,但仍然温和,谦逊,自制。我看到的他从来没有过度的情绪,永远温言细语,即使感到不悦也只是将微笑稍微敛起。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他高大挺拔的背影中,我却总是读出很深的,属于古典时代士大夫的痛苦。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
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唐涯
2017年5月10日
上海浦东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