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0
听报道
“ 文字的命运,就是时代的命运 ”——香帅无花
2017年我和“得到”磨课,经历过一阵非常痛苦的时期。我向来自诩文字不错,讲道理算是深入浅出,讲课绝不至于叫人腻味——但是在磨课时,音频里讲出来,总是有点“膈应”。我和我的主编都能feel到这点,但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要从哪里入手改进。
这个状态持续了很有一段时间,我在家里做困兽之斗,直到有天下午在网上闲逛,点开了视频《十三邀-许知远对话马东》,看完我窝在沙发上发半个小时呆,终于明白了自己的“膈应”在什么地方——
按照马东的说法,著书立说,这向来是“文人”的事。跌宕千年,识字的人从来只占社会的少数,加之印刷昂贵,能变成“文字”流传的必定出自“精英阶层” ——在中国,这个趋势的改变也不过是近几十年的事情,要知道,30年代全国7岁以上的人口中,只有30%的男性和1%的女性具有能够读懂一封简单信件的文化水平[1]。即使到了80年代,识字率也不过60%多。要知道,所谓“识字”也就是能看懂路牌的水平,和“读书写字”还是山海远隔——总之,写作这回事,在很长时间里,是极少数人和少数人的对话,那个姿态,是半自我陶醉,半催眠他人的。尤其是“说理”的文字,自觉处于理性的巅峰,更是矜持。
除此之外,和讲求“精确”的英文完全不同,中文注重“表意”。言简意赅,回味无穷的含蓄才是中文的灵魂。所以,中文写作中隐藏的原则是不能过于“直白”,过于直白就脱离“士大夫阶层” 了—— 不用否认,这点隐秘的阶级感是在我们每个人笔尖的,我也不能例外。出版界一直被认为是“雅”的世界,其原因也在于此。
这是士大夫文字的命运。让情绪宣泄留在民间,把理性说理留给庙堂。但凡是说理的中文,总是免不了的“俯瞰”视角或者“劝诫”态度——这是流淌在每个自以为“文人学者”骨子里的基因,你甚至无从回避。
可惜的是,我们遭遇了一个彻底解构的时代。如今的出版早不是“王谢堂前燕”,20多年强制的9年制义务教育后,10多亿人口95%以上的识字率,中国出现了全世界最大的“识字群体”—— 80年到90年代《故事会》,《知音》,《读者》的疯狂流行,背后正是这个识字群体的崛起。换句话说—— 中国“出版业”的主流调性,不再是“士大夫们”的浅唱低吟,而是这个群体的偏好所决定的。想到这里,你就会发现,郭敬明,唐家三少,被多少文人们痛心疾首的“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只不过是时代变化的结果而已。出版早就不是一咏三唱的阳光三叠,是街头巷陌平常人的平常物件而已。
在这种“解构”的浪潮中,只有一种文学始终放不下身段,这就是自觉高人一等的“学者文学”——这个身段放不下,倒也不完全是刻意为之,确实是内容和范式的双重限制:
首先从内容上来说,需要“逻辑推演”的说理性文章,多少有点“注孤生”的命运。这和人类的反射弧有关。在所有的写作中,词曲和小说是最“平民化”的,散文杂文次之:对故事情节,情感刺激的反射弧是比较短而直接的,因而容易引起共鸣共情,你去看,“杨柳岸晓风残月”可以娇滴滴唱一咏三唱,《三国演义》可以声情并茂让人拍案惊奇,就算鲁迅吧,被人记住的也大多是“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这样掷地有声的铿锵之语。但而被誉为中国历史上体系最完整的文学批评理论专著的《文心雕龙》,包括我这等伪文艺女青年在内,也大多没有看过原文(坦白说,看过,觉得犹如嚼压缩饼干,没看下去)。为什么?因为刘勰写的时候就没有打算给你我看——这是文人间秘而不宣的对话,一招一式,都充满隐秘的过招的快感。这个快感,与你我普通人的生活情感无关。更何况“逻辑”,从来不是擅长表意的中文的长项(P.S. 这是另外一个极度有趣但是复杂的问题,此处就先略去)。
此外,从形式上来说,“学者文字”本质上是一种职业化程序化的写作。古代中国的“学者”是从帝王视角研究国家治理之道,尤其自隋唐科举制之后,催生了一个“学而优则仕”的行业,而任何“学问”一旦行业化,就必定以文本化标准化的方式出现,否则无法复制和推广。有时候想想“八股”挺冤枉的,这个被大家所诟病的文本范式,其实是庞大科举行业的基础设施,养活了大批批评它的人。
现代中国之后,我们匆忙引入西方科学体系,毋庸置疑这是历史的转折点,但问题又来了,无论是教育体制还是语言体系本身,从根本上说,中国学子是缺乏逻辑训练的,所以特别容易削足适履。尤其进入工业化时代之后,科学学科体系发展加上教育产业化,产生了对一套标准化学科评判体系的需求——学术发表制度以及相适应的写作范式。我们通常称为“学术洋八股”。倘若以“学者”为职业就必须学会这套语言交流体系,否则就自动出局。这套范式非常专业化,基本上隔行如隔山—— 比如说,你让我去看篇其他学科的纯学术论文,也跟天书差不多。一方面你很难批评这种范式,因为这是学科体系和教育产业化发展的需要。但另一方面,它的后遗症也是明显的,因为语言和写作都是非常路径依赖的过程,很难在两者中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点。日子一久,学者行业逐渐丧失了对“沟通型文字”,尤其是大众沟通型文字的审美以及把握能力。即使想写点“面对大众”的文字,要么是读来味同嚼蜡,要么是晦涩不堪。偶尔有几个能把话说明白的,大家就觉得相当惊喜了。
尤其是这些年经济金融成了“显学”,学问的市场起来了,能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却是寥寥可数。换句话说,我们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空白地带:学问,尤其是社会科学的学问,本来是替“社会”做的,但是社科的学者大都丧失了和“社会”对话的能力。
不是不想对话,只是路径依赖,缺乏了和大众对话的能力。即使对话,也是范式和惯性驱动下的“学者文字”。早期信息不通畅的时候,忍忍也就算了,如今信息过载,飞速迭代的社会中,这种“学者文字”就变成了一种奇异的存在,就像大清早亡了,偏生留着辫子,裹着脚一般,说不出的尬。
这是件挺伤感的事情:一方面,看到《货币战争》这样的通俗演义型金融小说,被当做“正史”甚至“资料”来被研读追捧,是冷汗直冒的,但另一方面,确实市场上“既严谨还有洞察还说人话”的资料确实是寥寥可数。我2010年回国后苦于对中国经济缺乏“体感”,想找点东西看,最后真正给我一些体感的反而是一些资深记者,比如吴晓波《激荡三十年》这样的作品。
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对自己的“膈应”已经有了答案。应该说我算是只“黑羊”,因为从小文字感觉不错,所以从2013年写专栏,到2015年开公号,一直算是试图在恢复这种“对话”能力,但是很多东西,在你骨子里沉淀了十多年,尤其在你写字生涯里被反复训练打磨,早就是“条件反射”,尤其是当从“书面表达”下沉到“声音表达”这种模式的时候,其实我是本能抗拒的。
为什么抗拒呢? 因为在书面表达的时候,我只要调整“视角”,寻找“共情”,对于一个像我这样文字驾驭能力不错的人来说,这在根本上还是一个相对舒适的领域,是一种语言和结构的重组。而且,“阅读”是有主动性的,大逻辑顺畅,中间细微的逻辑断层不太会影响读者,所以作为作者,你需要对抗的,是你自己的惯性和窠臼—— 这很难,但不是最难的部分。
当开始“声音表达”的时候,你有两种选择,一是放弃逻辑,以情节或者情感动人(就像收音机时代的评书或者半夜悄悄话),假设你不能放弃逻辑,希望说清楚一个道理或者体系,你要对抗的就不再是自己,而是“注意力”这种无影无踪的稀缺品。这个过程中,不但大逻辑,即使最细小的逻辑你也不能轻易断层,因为断层就相当于打断了“对话”。换句话说,你必须彻底放弃“我”这个预设,而从对方角度出发去进行“对话,否则就变成了“尬聊”—— 对于一个习惯了上帝视角的学者来说,这才是最难的事情。
而马东v.s.许知远, 忽然以一种几乎鲁莽的方式,将这个选择推到了我跟前。
马东斩钉截铁的说,“我们曾经精致过吗?”(这是回答不是问句),“ 文化是结果,不是过程 ”
许知远看着远方飘忽地问,“我们至少曾经向往过这种精致吧 ”。
差异那么真实的摆在了我面前:马东在“对话”,许知远在“跟自己说话”,所以我们会觉得许知远在“尬聊”,但是换位思考一下,我眼里的许知远的“尬”,何尝不是自己的“尬”呢?
原来写专栏这么多年,我面上去了“学者文字”的外衣,其实思考方向其实没有变,还是“自我”或者“同行”视角驱动的,是自己独白,或者对某个特定群体的陈述—— 换句话说,内心深处,我还没有做好和“非同行”交流对话的准备,而形式上我又需要这个对话,所以听上去的“膈应”,大概就是许知远在屏幕上显示的“尬”—— 身子在“对话”,思维却“在别处”。
想通了此节,我回到桌前时,突然卸下了一个包袱,我也说不清的包袱,大概就是突然从站着讲课的姿势跌落回沙发,和对面人“对话”的感觉吧,这种对话,不是漫谈,而是一种需要找到答案的,有焦点的对话。找到这个感觉之后,磨稿的工作突然顺利起来,中间自然还是各种磨合,但是那个“方向”或者说味道是找到了。
顺是顺了,但是我却没有仔细琢磨,只是隐约感到文字的命运在发生某种奇怪的转变。这里面深层次的逻辑一直没有思考清楚,一直到读到一本书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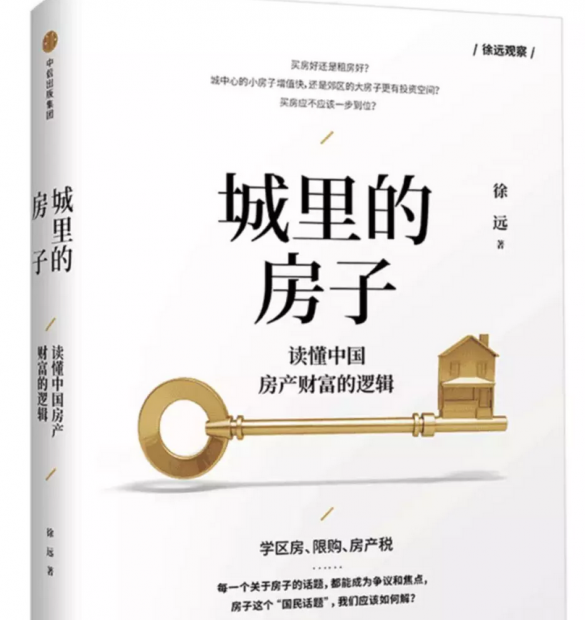
这是徐远的新作《城里的房子》,这是我读过的最接近“自然状态”的一本“学者之书”,所谓接近自然状态,就是放下了惯常的经济学者要“经世济民”的身段,心里想的,手里写的,嘴上讲的都是帝王将相的“屠龙之术”,尽管世界上没有那么多“龙”可屠。
这是一本从普通百姓视角出发的“房术”,这十来年中国人最闹心的“房事”,很多解答都在里面。
房价又涨了,到底还能买吗?
这点破钢筋水泥把我积蓄全搭进去,到底值不值?
攒了点钱能付北京五环一个小公寓的首付,我妈让我回老家买个大房子,我该怎么选?
我想一步到位在城郊买个明亮大三居,老婆宁可要城中心的老破旧,我们两谁更有道理?
手里有点钱是干脆付了全款,还是分期付款划算?
我好哥们在泰国海边买了个小公寓,又美又便宜,是不是在太泰国买房比在中国强?
好多专家说租房更划算,因为中国“租售比”比国外低好多,这租售比到底怎么算?
……
一桩桩,一件件,都是我们老百姓生活中面临的实际选择问题,这些问题无比切身,而市场上的很多自媒体文章,大多是缺乏数据和框架的“结论”,既不给出数据的分析推理过程,也缺乏自洽的逻辑。而谈到“房子”的学者文章,一是寥寥,即使有几篇,也是“屠龙之术”,绕着弯子讨论“过去房价”的决定因素,再辅佐以晦涩的文本和模型,对于现实里最焦虑的选择问题,几乎就是望梅止渴。
徐远教授这本《城里的房子》,是学者之文:近十年土地制度,城市化,和中国宏观的研究,
对中国金融市场和资产定价的研究,以及大量严谨的数据分析—— 形成了一套以增长和城市化为底层逻辑,以动态资产定价为比较工具的房价分析框架。
但是这本《城里的房子》,又是放下身段说人话的学者之文:它不跟你谈宏伟的国家战略,看波澜壮阔的周期,只是真正从“普通家庭”的视角和痛点出发,跟你跟你娓娓道来,剖析那些让我们糟心又焦虑的“买房租房那点事”。
这不奇怪,因为这是一本从“对话”开始的书。我得到课程期间,因生孩子请徐远教授代班讲了两周课,其中一周就是春节期间的房地产特辑,当时我已受到马东和许知远这场谈话的刺激,大体知道了行文视角会带来文字基因的改变,所以这周的房地产课程,就是百姓视角的“对话思维”。之后,徐远老师将这一周课程,结合之前自己的研究笔记,和对后台近万的读者问答里选取的“典型问题“尽力给出的严谨诚恳的回答,扩展成了一本关于百姓房产财富的书,取名为《城里的房子》,理由也很简单—— 因为
“人类演化的一条轨迹,就是离开土地,汇聚成城”。城里的事,就是百姓的事,城里的房子,就是普通人的房子。
是为荐。
读完这本书稿之时,恰逢我得到一年课程的结束之日,想起了当时看《十三邀》的冲击和感受,这才坐下来回想,到底文字这点事情在发生什么样的改变。
或者,一个平民学问的时代来临了,第一次学问不需要宫廷的或者机构的供养,而可以扎根于普通人的土壤—— 中国十三亿百姓,他们的问题,才是学问的导向和根源。用学术的方法,做百姓的问题,用普通人对话的语言,解答百姓的问题,这才是文字的生命力,至于是不是可以被沉淀的“文化”,不必系怀,让答案,在时间的河流里去浮现。
想到这里,我猜,自己可以回答自己关于文字命运的问题了。
文字的命运,就是时代的命运。
注:[1]这个数据来自被广为引用的卜凯在30年代初期对中国农村的调查。
话题:
0
推荐
财新博客版权声明:财新博客所发布文章及图片之版权属博主本人及/或相关权利人所有,未经博主及/或相关权利人单独授权,任何网站、平面媒体不得予以转载。财新网对相关媒体的网站信息内容转载授权并不包括财新博客的文章及图片。博客文章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财新网的立场和观点。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