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金融导致东西方大分流?
著名的金融学者James Macdonald曾做过研究(《A free nation deep in debt: financial roots of democracy》),他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历史现象。如果我们把公元1600年的国家分为两组,你可以发现,一组国家是藏宝于国库,中国的明朝国库的白银有100多万两,印度是6000多万两,而土耳其帝国的藏金是1600多万块。另一组你会发现是负债累累,英国、西班牙、法国、荷兰、意大利等城邦国家,这些都是天天在外面借债、发债的国家。但是你会发现,从公元17世纪到20世纪,400年间,历史发生了奇妙的逆袭。这些负债累累的国家,现在基本上都是发达国家,而那些曾经的“财主帝国”都变成了发展中国家。
我们如果以人均的GDP来看,中国在公元1000年到1200年间(宋朝)达到了顶峰。之后的1000年就开始停滞不前。而隔海的欧洲,从无法望中华帝国之项背,到走出黑暗的中世纪,一直保持着非常稳健的增长。而这个转折点,不是大家以为的发生在17世纪,而是发生在12世纪左右,也就是欧洲的债券市场开始起源的时候。
所以,尽管很多人仍然把十六、七世纪作为东西方大分流的开始,但是最近的学术界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在12世纪左右,东西方的分流已经开始。其中,驱动力之一就是金融模式的分流,西方的财政金融体系开始大规模地使用国债,而中国依然主要依赖财政税收体系。
为什么发债与否的金融模式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呢?这里我们首先要看看发债的目的是什么,发债这个手段的替代品又是什么。
国债发行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替国家融资,解决国家的财政支出。现代社会的财政支出你一定知道,主要是国家的公共服务,包括国防军事、司法、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等等。那财政收入的另外一个来源是什么呢?自然是你很熟悉的税收。
税收和发债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呢?
首先是资金筹集的时间概念不一样。税收是一种财政手段,针对的是当下的居民收入,相当于“切蛋糕”,重新在政府和居民中间分配资源,然后居民的份额就变小了。而发债则是一种金融手段,用国家的未来收入做抵押,相当于“借面粉”,将未来的蛋糕做大再进行资源分配。换句话说,发债是一种以时间换空间的融资模式,尤其是当民间的投资回报率超过国债的利率时,整个社会的财富就是增长的。
在我们刚才举的这些例子里,这些欧洲小国通过发债,将未来的收入转移到了当下,平滑了国家在不同时期的资金需求。所以,避免了一次性征税对于社会,对于居民产生的冲击。而你一定知道,税负过重,民不聊生,往往是一个国家动乱的根源。
实际上,从现代来看,这种多发债少征税的思路也正是美国崛起的金融逻辑。政府通过发债,从国内外吸收廉价的资金,让居民手里的资金份额更大,通过投资再实现整个社会的财富增长。
除了资金筹集的时间概念不同之外,债和税的第二个区别是契约关系不一样。税收是全民性的,强制性的,而发债是局部性的,契约化的。这种选择既和各个国家的政权模式密切相关,又对各个国家未来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一个事实是,那些“藏宝于库”的大多是中央集权式的帝国,而那些通过举债藏富于民的大多是分封制环境里成长出来的欧洲国家。
另外一个事实是,人类历史上,像二战以来,长达70年的和平时期是很罕见的。大部分时候,人类社会都是金戈铁马,抢夺资源,所以战争开支是各个国家最大的财政支出。而税收需要依靠强大的国家暴力机器,一旦遇到大的战乱,税收很快就会导致涸泽而渔,民不聊生,而造成帝国解体,或者是改朝换代。
而欧洲国家,一直处在激烈博弈的状态中,它缺乏大规模的征税能力,只能借债。而且因为整体社会比较穷,所以早期欧洲国债的购买者并不是普罗大众,而是那些掌握着大量资源的富有家族。比如说欧洲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就曾经是英国国债和美国国债的最大买家之一。所以国债用一种契约的方式,把这些贵族手里的资源进行了时间维度上的优化配置,同时也实现了欧洲各种政治力量的制衡。
所以,国债是以契约关系,明确了居民和国家中间的债务关系,允许国家以未来信用做抵押进行融资。一个具有流动性的国债二级市场,把国家信用从虚拟的概念转化为可以循环使用的活水,这些变化对整个现代国家概念的塑造有着重大的意义。为了保证债权债务关系的清晰,这就需要一套法律制度来维护这个契约的执行,所以国家和政府的权力就会受到限制和约束,欧洲的契约社会和法制社会也就这样开始慢慢形成了。所以,从金融的角度看,东西方大分流的李约瑟之问就似乎已经有了答案。
我们国家在明清以后,传统社会的形态更加趋于稳定,财政危机周期性的发作,到了不可收拾之际,就以王朝更替结束了。而欧洲的各国,学会了“向未来融资”的金融手段,获得了强大的资金支持,使他们能够向外扩展,掠夺资源。同时民间的力量发展起来,社会的流动性增大,极大地激发了社会的创造力,为工业革命奠定了物质和思想基础。
在两种金融模式的驱动下,国家的力量此消彼涨。到19世纪的时候,世界格局已经彻底地被改变了。欧洲在现代社会的几乎所有领域,科学、文化、政治、经济都已经将曾经的中华帝国远远地甩在了身后。
二、中国王朝更替的金融逻辑:债务逻辑
从金融的角度来看社会的演进是个非常有趣的过程,细节复杂,但逻辑简单。比如说,如果我们试着从债务关系的角度来解构中国历史,你会发现,王朝更替几乎都是原有债务关系的破裂,新债务关系的重构。
或者你可以这么理解,国家和民间债务关系互相影响恶化的“债务螺旋“是中国王朝更替的金融根源。
尽管社会上的债务关系纷繁芜杂,但是按大类分无非是国家、企业、个人三者中间的一个债务网络。在农耕经济的古代中国,这个网络就可以简化成国家和个人、个人和个人这两类债务关系。国家和个人,也就是居民中间的债务关系主要体现为各种税负。在这个债务关系中,你可以将国家政府理解成债权人,居民是债务人。税负越重,居民对国家的负债就越高,也就是杠杆率就越高,而且这个债务的违约成本是很高的,不纳税可能会被送进监狱。

除了国家、个人中间的这个债务关系之外,另一种债务关系就是民间的个人和个人中间的债务关系。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量入为出是基本准则,所以民间的大规模借贷一般发生在青黄不接或者是天灾人祸的时候。这个时候很明显,债务人会处在绝对弱势的地位,所以他需要承担高利息和非常苛刻的抵押条件。中国的民间利率都是按月度计算的,一般所谓的三分息就是指月息3%,年化利率能够达到36%,而抵押也一般是超额抵押,经常会包括房屋、土地,严苛的时候甚至包括妻子、儿女等。
所以这两种债务关系就构成了传统中国社会的基本形态,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一个三角形,它的稳定程度就取决于这个三条边的杠杆率是不是适度。
而从传统中国社会自给自足的经济特征来看的话,一个相对健康的社会环境就应该是杠杆率比较低的社会。比如说税负低,它就可以保证适度的“藏富于民”,让民间休养生息,能够自给自足,为扩大再生产做储蓄。你看,历史上的盛世前夜无不具备这样的特征,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甚至是政治集权达到顶峰的清朝康熙年间,税负和民间借贷都处于比较低的水平。
而从另外一个维度想,从汉朝以来中国就是以一个相对简单的官僚治理结构,管理着一个庞大和复杂的帝国,所以“维稳”是历朝历代的刚需。而“维稳”是需要成本的,在这两种关系中,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都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所以杠杆率一高,社会的张力、社会的摩擦就会变大,“维稳”的成本就会急速地上升。所以“低杠杆”是中国社会维持稳态结构运行的一个必要非充分条件,也是传统中国社会“去金融化”的根源所在。
然而,所谓的稳态结构其实是不稳定的,因为一旦有外生冲击,比如说天灾人祸、外族入侵,这两种债务关系就会迅速地恶化,形成一个杠杆率交替上升的“债务螺旋”,将这个稳态结构打破,最后以王朝的更替结束。

以我们最熟悉的明朝为例,明朝虽然延续了300多年,但是从朱元璋开始,它的社会张力一直比较大,它不是一个自然维稳的状态,而是靠庞大的集权和行政体系来强行维持的。那为了维持这么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国家就必须多征税与民争利,同时因为民间财富被挤压,在靠天吃饭的年代里任何一点点自然灾害,旱灾、涝灾、虫灾都会造成民间杠杆率的大幅度上升,债务关系恶化。民间债务关系恶化的极端表述就是“民不聊生、揭竿而起”。
从朝廷的角度来说,民间债务关系的恶化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维稳成本急速上升,所以财政又会出现巨大的缺口。那财政出现巨大的缺口以后,朝廷没有其他的办法,只能加重税负,提高国家对百姓的杠杆率,从而又导致民间债务关系的进一步恶化,更多的社会动乱出现。你看,这样下来,两种债务关系就互相加强恶化的趋势,杠杆率也交替上升,一直到这个稳态的结构被彻底打破。
明朝后期的时候财政已经比较困难,到崇祯皇帝上台的时候北方又碰到大旱,导致了游牧民族生存很困难,只能来攻打中原,所以明朝的军费开支就大涨。这个外生冲击逼得崇祯皇帝只能够加税,在原来九厘税的基础上又加了三厘,所以民间的压力陡增,平时为了应付军事压力,崇祯皇帝还大幅地裁减“公务员”,全国的驿站当时缩减了1/3。其中有一位“失业的公务员”叫做李自成,他收拾铺盖就回了陕西老家,更不幸的是这一年陕西发生了大旱灾,卖儿子、卖妻子的情形非常普遍,民间的债务关系恶化得非常厉害。李自成也是这个民间债务关系恶化中的一环,他借了债还不起,然后被债权人告到衙门,差点被处死,幸好被亲友救出来。然后李自成出狱以后,一怒之下一刀把他的债主就给杀了,欠债又杀人,然后就怀着满腔的仇恨投奔了起义军,成就了历史上最有名的李自成起义。
起义军一路势如破竹,逼迫朝廷必须加大军事开支,只能进一步地压榨民间,以各种名义收税。那税负的加重使得民间的债务关系进一步地恶化,逼迫更多的“李自成”加入了起义军,两边的杠杆率相互交织,螺旋式上升,一直到明朝的这个稳态结构不可承受,走向溃败。这样也就使得北方的游牧民族有机可乘,清军入关,朝代更替。
明朝的这个例子其实在中国的历史上一点也不新鲜,历朝历代大多是因为这种“债务螺旋”,导致社会的维稳成本升高,一直到当朝的政权不可承受。秦的覆灭、唐的衰落与宋的更替、元的消亡,无不是在这个“债务螺旋”下的故事重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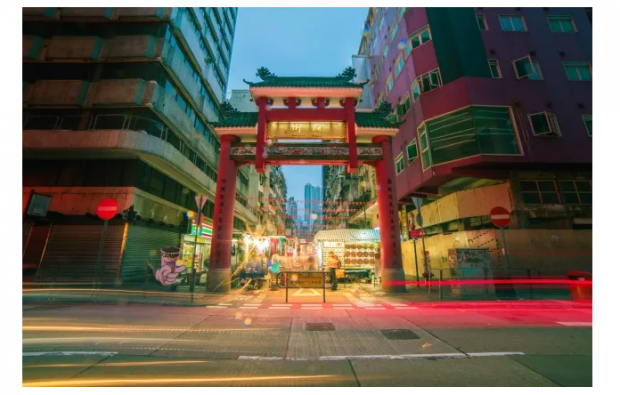
更有意思的事情是,历史其实总是在不断地重复自己,每次王朝的更替之后,新朝廷一般会干两件事情:第一是大赦,除了赦免犯人的罪行以外,就是废除前朝的一切债务,相当于强行“去杠杆”,用强制的办法理顺民间的债务关系;第二件就是减税,休养生息,去理顺国家和居民中间的债务关系。这两个举措我把它称为“双降”,也就是同时降低国家和民间的杠杆率。整个社会的杠杆率下降以后,社会会渐渐地恢复到原有的稳态结构上,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之后盛世就逐渐地出现,一直到下一个冲击的出现。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